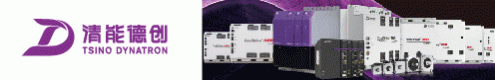不过,在业界看来,这些规定多为临时性、指导性规定,涉及具体监管细节相对滞后,目前国内尚未形成完整的民用无人机规章及管理体系。
一位从民航系统出来创业的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无人机领域以前是没有部门愿意管,现在是大家争着管。比如无人机一方面属于民航局管,同时空域安全涉及空军方面,产业政策涉及工信部,其他如公共安全还涉及公安部,具体行业应用还涉及其他部委。
目前国内无人机的政策配套落后、监管缺位,低空空域开放步伐缓慢,缺乏相应的产业标准是公认的事实。
在法律界定上,民用无人机是否属于航空器目前没有明确的规定;在空域管理方面,现有相关文件缺少具体流程、未明确具体管理部门,只笼统地对民用无人机的空域使用进行说明;在行业标准方面,并未形成统一权威的研发、制造和设计标准。在产业管理方面,也没有市场准入标准和法律法规。
游说监管
“如果我是生产菜刀的,不能因为菜刀可以用来杀人,就禁止我卖刀。”大疆创新副总裁王帆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和很多无人机企业一样,企业人士的公开表态,都是呼吁出台监管政策,维护市场秩序,同时也表示,希望监管最后形成的结果,是让大家都能有序的去飞,不能用政策去打击大家的热情。
“希望是去呵护这个产业,而不是用懒政去一刀切。”王帆说。
从全球范围来看,美国的无人机监管政策走在前面,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多是在参考甚至照搬美国的政策。
2015年,美国出台了无人机监管的系列政策,包括无人机必须进行备案制度,另外每一架无人机必须配备一名专业操控人员,必须获得相关的执业牌照,另外无人机必须在操控员的视线之内飞行。
有企业认为,这些监管规则过于严格。其中以致力于发展无人机物流的亚马逊公司为代表,意见最大。2015年4月,亚马逊向FAA(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致信,督促后者放宽无人机测试规定。
相对来说,国内的监管还在初级阶段,对于政策制定方来说,遇到的问题也都是新问题。2015年底,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在例行记者会上表态,无人机不能无人管,相关部门正在研究制定系列法规和标准。
FAA出台了一系列针对无人机的政策,近期还在做不断的调整。监管对产业的影响不言而喻,从大众媒体上,可以看到很多企业参与和游说的身影。
比如中国大疆无人机参与的“小型无人机联盟”,即是一个产业游说团体 ,致力于促进 “修改商业、休闲及慈善用途无人机的政策和法例,容许无人机在一定程度上自主控制的视距内飞行”。
王帆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原属于联盟成员的大疆 、3D Robotics 、Parrot 和 GoPro,刚一起退出联盟,另组 “无人机生产商联盟”(Drone Manufacturers Alliance)。
王帆透露,退出的原因,即无人机类型千差万别,不同类型无人机的利益诉求,也是千差万别。所以“和平分手”,重新组队,做“更符合自己需求的事情”。
王帆总结,当下中国关于无人机的政策,正处在一个敏感纠结期。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发现,在政府政策制定的过程中,企业、行业协会以及政府各部门的博弈,也是各方逐力。
同样在推进无人机送货下乡的京东集团,已经与两个县达成合作,在当地推行无人机送货试点,政策也是该项目落地的主要瓶颈。
京东方面透露,一方面积极试点,同时也在关注政府政策的制定,积极参与相关行业标准的设立。
一家江苏企业负责人认为,当下比较活跃的大企业,资金和公关活动能力较强,在制定政策过程中有很多话语权,但小企业的声音容易被淹没。
他希望政府在最终出台意见之前,能充分听取各类型企业的意见,特别是能兼顾一些规模不大,但具有核心创新能力的创新型企业。
政策变数
处于“纠结敏感期”的无人机产业,遭遇正在制定的监管政策,或许成为产业发展的重大变数。
亚马逊发言人多次公开吐槽FAA的政策,其发言人Paul Misener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亚马逊无人机面临两大挑战,技术与监管,但相对而言,监管政策问题更难把控。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国内一些无人机企业时发现,各方对监管政策的看法和利益诉求各不相同。前述大疆无人机退出“小型无人机联盟”,另立新组织,也证实了各方意见的分歧。
亚马逊的观点更多代表了发展物流应用的无人机企业观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部分国内消费机、农业植保机厂商,对监管政策持相对“审慎乐观”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