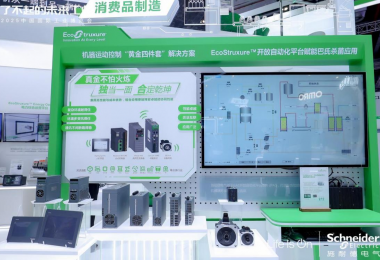我的一个很大的弱点是,一辈子不大爱交朋友。喜欢特立独行,工作之余喜欢独处。呼朋唤友,拉帮结派时少。有人说与我的血型有关,比较各色。但一辈子毕竟与人为善,自认为与我算得上朋友的,倒也不少。
让我真正体会朋友这个词的意义的,是在我06年倒霉的时候。那个时候,原来企业的老板为了治我于死地,竟动用了司法工具,双管齐下,在长达7个月的时间里,堂堂共产党的司法机构竟然成了这个企业的御用工具,几乎每个月把我叫去一次,非要查出点问题不可━━据说他们很奇怪,“一个当了五六年总经理的人就不信一点问题都没有”。在皇城根儿下,居然还有如此有罪推断的司法机构,大大出乎我的意料。虽然明知自己清白、无辜、终究没事。但一位朋友提醒了我:在中国,冤枉一个人算什么?刘少奇、彭德怀又怎么样?为了救赎自己,为了躲避可能的拘留,和妻子开始寻找一切能帮忙的朋友。
能证明我清白的,首先是与我共事的同事们,尤其是在原来的公司里仍然身处要职的同事们,我们共事最短五年半,长的有20年,他们大都是经我多年栽培和提拔的,他们的股票大都是我向大股东争取的,有的连妻子都是我的爱人给介绍的。当我和我的爱人请他们证明一个极为简单事实的时候,他们或者直接拒绝,或者支吾躲避、唯恐惹祸上身。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大股东捏造一个莫须有的证据之后,他们居然一一签字,这是我最难以接受的。不必说知恩图报,甚至在事情未明之前保持沉默都可以理解,但明知害人仍然去做,事后有一万个解释都无济于事了。庆幸的是,人间总有良知在,其中有两位同事在那个关键时刻毫不犹豫向司法机构写出证言,证明我的清白。经此一事,我把这两个人以及当时没有投井下石的,都当做朋友。
我一位远在哈尔滨的高中同学得知此时,比自己的事情还急,几乎一天一个电话,为我们推荐律师,提供各种可能有用的关系渠道,他还这样安慰我的妻子:“玉琢不会有事,我了解他。要说我们这些政府官员吃点、喝点都有可能,玉琢连这个都不会有。”他介绍的一位律师朋友,后来成了我们正确分析形势,采取正确对策的最重要的谋士。在那个时间段,我只能靠爱人与外部联系、奔走。爱人的头发开始脱发,其压力之大可想而知。此时,我大学的一位女同学从唐山经常打电话给她,起到很大安慰和温暖的作用。
在我需要躲避无妄之灾的重要时刻,我首先想到的居然是远在大连的一位业务伙伴。他得知我的情况,没有表现出半点为难之色,在他那里住了四天,他每天抽出大把的时间陪我吃、陪我玩,试图让我忘记眼前的忧愁。当我要到三百公里之外的哥哥家住几天的时候,他不顾自己的严重感冒、发烧,亲自驾车送我。后来他才告诉我:“你知道那天为何带一位同事一起上路的吗?你一定以为是我为了路上解闷儿,或者怕路上累着,其实都不是。我是准备一旦因为你出事了,我的车好有人开回去。”
其实我能坚定的加入金风,也与此时有点关系。我到金风报到的第十一天,公安局就来电话传唤我,金风的主要领导人得知后是这样告诉我爱人的:“李总只要在金风干一天,就是金风的人。需要钱,写个条子就可以。需要律师,马上安排去商量案情。”果然,第二天一位律师就赶到我躲难的宾馆。我在金风工作期间虽然也遇到许多的困难,但我坚持下来,其中的一个因素,就是金风对我的知遇之恩。
在帮助我的人里面还有两个重要的人物,是我在四通时的同事和领导,他们听了我爱人的哭诉,利用一切社会关系积极为我奔走。在一次司法机构的朋友聚会上,我的老领导用这样的话为我解脱:“听说你们最近在处理李玉琢的案子,他与我共事八年,我很了解他的人品。如果有事,我绝不袒护;如果没事,希望各位不要为难他。”后来因为这个案子反而成了我们朋友的一位当时在场的司法部门负责人告诉了我们这个情况,我对此一直觉得感激与不安。
所谓不安,是因为在我的《我与商业领袖的合作与冲突》一书中,我还几乎把他描写成一个“坏人”。但关键时刻,他说了公道话,而且起了作用。
今天我写这篇文章,是为了永远记住那些难得的朋友们。同时也提醒自己,真正的朋友不是在平常的日子里与你称兄道弟的人们,而是那些在面临危险时还能助你一臂之力,还能送来同情、安慰与温暖的人们。而对于那些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对不起你的人们,忘记他们,让他们自己去慢慢体会人间的正义、良知与真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