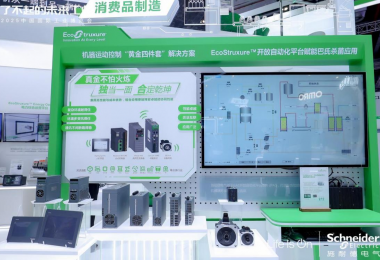办个企业叫“深通”
我从北京合资公司抽调了四五个人,记得有范为强、丛敏、王植柄、周怡军等,一起南下深圳,创办深通打印设备有限公司。
四通在销售打字机的过程中,发现打印头是用量比较大的消耗品,而给用户换打印头上的一根针就一百多块钱,潜藏很大的商机。于是,就借口增加国产化比例,要求把打印头的生产和打印机架的组装也从日本转移到中国,就像当年把打字机的生产转移到国内一样。
打印机架的国产化组装工作之前已经在北京的合资公司做起来了,现在是更深入的一步——把打印头的生产组装也转移到国内来。但这件事光三井说了不算,还必须把富士通拉进来(打印机的机械部分属于富士通)。
深通公司的名字还是我起的,意思是深圳的四通。注册的时候,四通集团占51%的股份,日本三井公司占25%的股份,日本富士通公司占24%的股份。深通公司从日本进口打字机机架、打印头及打印针等散件,利用进口的一些专用设备组装成打印头和机架的半成品,经过测试后,再把打印头组装在打印机机架上,成为一台完整的打字机芯,然后卖给北京四通办公设备有限公司(SOTEC),组装成一台完整的MS-2401打字机投入市场。我任公司总经理和董事,段永基任董事长。公司位于深圳八卦四路。
这是我第一次担任一个独立公司的一把手。而且因为“山高皇帝远”,四通高层很少来这里,所以也很少干涉我的工作。从办企业的角度来说,深通公司的三年是我非常宝贵的经历。这也算是因祸得福吧。
创办北京合资公司的时候,我跑过营业执照,安装过电话,改装过厂房,组织过生产,主持过南北SOTEC两个企业的日常工作;后来担任OA本部部长,又管过销售和服务,所以已经有了一部分办企业特别是办实业型企业的经验,但毕竟是给段永基当副手,OA本部也只是管理一个营销环节。创办深通则不同,我不仅把所有办企业的程序重新来过一遍,而且基本是最终的决策人。那时我在自己的办公桌上立了一个牌子,上面是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一句话——“责任到这里为止”。
公司建设期间,选择厂址、地上画线、装修等基建筹划工作,都是我亲自带领同事们完成的。记得当时在一个空厂房里画线的时候,厂房缺氧。我画了一会儿,居然喘不上气,虚汗直冒。我问其他人:“你们有什么感觉没有?”他们都说没有。于是我到窗口呼吸了一会儿空气才能接着干。现在想来,缺氧也许是我后来得冠心病的先兆。可以说,深通是我一砖一瓦建起来的,我一直把它当成亲儿子一样看待。
一个人只有放在企业老总的位置上,才有可能系统地全面地考虑、处理问题,才有可能磨炼出企业家必备的胆识和能力。
当时面对很多问题,包括进口、采购、通关、报税,生产组织,行政后勤,财务制度,怎么搞好员工管理,生产质量上怎么做,以及如何建设企业文化、怎么样让员工有凝聚力等。企业本身的内容以及客观形势迫使我不得不考虑这些问题。
深通公司的人际关系非常简单。那时候大家大都单身在深圳,下班后员工们打球、下棋、甩几把扑克,然后到金威啤酒屋,围成一桌,叫几碟凉菜,一人一扎生啤酒,喝得痛快极了。那时候在深通生活、工作都比较快乐,甚至让我痛苦了好几年的前列腺肥大都好了。
后来还成立了员工俱乐部组织各种活动,俱乐部主席、副主席由全体员工公开投票选举产生,任期一年。每一次竞选者都需要登台演讲,张林、杨泓、梅秋生都被选上过。
考虑到员工的未来,深通公司还有一个政策,鼓励员工业余时间学习,凡拿到结业证书的,学费由公司承担。这样一些活动使深通这个企业大有家庭的感觉。那时候大家的工资都不高,但公司的氛围非常的好。在深圳,人们把员工称作打工仔、打工妹,深通的员工没有被人瞧不起的感觉。
同时管理上也比较严格,记得深圳出现股票风潮的时候,从公司的窗户就能望见抢购股票排队的人群。公司严格规定,任何人因买股票排队等原因影响工作的,除名。一直到今天我都认为,一个人把钱投到股票市场上,让他专心干好本职工作是不大可能的。
公司还遇到一件棘手的事。春节放假要求员工按时返回岗位,耽误一天开除。结果工作出色的胡金茹买了车票没挤上火车,第二天买了一张飞机票赶回深圳。怎么办呢?公司的规定总不能因此不作数。我想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胡金茹照样开除,但允许在公司试用一个月,表现好可以重新转正。
我适合这种文化氛围,也创造了这种文化氛围,后来还把这种文化带到了利德华福。记得在华为的时候,任正非曾当面批评我玩扑克是“玩物丧志”,我当时就发了一个誓:将来我办了自己的企业,决不采用华为的文化!
就是这样,我按照自己的思路去理解企业,按照自己的理解去管理企业,按照自己的理想追求去建设企业文化,按照自己的目标去寻求企业发展。深通给了我独立操作企业的舞台。我充分理解了靠什么、该如何去办一个像样的企业。
处理走私事件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深圳是个走私成风的地方。我刚到深圳的时候,有人就告诉我,在深圳,企业不走私就赚不了钱。我当即反驳道:“如果走私才能办成企业,这种企业没有必要办。我也不会干这种事。”我告诉他们,道理很简单,走私的钱归个人吗?不归,走私赚的钱都是公司的,可是出了事抓起来的是谁呢?是我,这样的傻事我为什么要干?
我碰到的第一件走私的事,是1989年6月底我刚到深圳索泰克转移打字机生产的时候。公司前任负责人把进口的一批打印机以非常便宜的英文打字机的名目报关,结果事发。这位负责人一到东莞海关就被扣下了,他借口向外面的司机交代点事,趁机逃跑了,司机被抓住蹲了28天。好在这位负责人走私时是用一个承包的贸易公司的名义签的合同,深圳索泰克没有牵连进去。而那位负责人被通缉、逃亡期间,女儿病死,老婆离婚,真正落得家破人亡。
1992年在深通,我又碰上了一次“走私事件”。
那时深通组装打印头和打字机架的零部件都是从日本直接进口的,只有一些集成电路芯片从香港进口。有一次,我们从香港采购了10万元的芯片,正要去办理报关,没想到对方的送货人背着装有芯片的袋子直接过关时被海关扣住了。海关问他芯片是给谁的,他说深通公司。海关便以为是深通公司走私,通知深通公司派人去海关处理问题。当时集成电路芯片的关税很低(7%),10万元的芯片不过7000元关税,没有人会走私这种东西。我当即安排主管生产的副总经理范为强去海关看看情况,范为强说他也没处理过这种事请,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心里明白:其实他是不敢去,怕被抓起来。这种情况下,如果我再派别人去显然不合适,要是再推辞不去,岂不尴尬?只有我去。很多人听说我要去,坚决反对。他们以为去的人肯定回不来了。我安慰大家说:“放心吧,不会有事的。如果我进了监狱,你们知道我是为公司的事被抓的,别忘了给我送饭就行了。”
到了海关询问了情况后,我告诉海关人员:我们的报关单都填好了,没有谁通知对方闯关;如果是走私也是对方走私与深通无关;问题是有没有人会傻到为7000元走私?我们的公司不是个人的公司,省下这点钱又不归个人,我们没有为此走私的任何理由。
听了我的一通解释,海关人员点了点头说:说一千道一万,毕竟还是走私吧?这样吧,罚你们点钱就算了。经过我的一番据理力争,最后以罚款1万元了事。
两个小时后,我平安回到公司。
与日本人的几次较量
四通的发展一直没能脱离开日本企业。无论是南北索泰克,抑或是深通公司,都有日本三井的股份。后来又与富士通、OKI、ALPS、OMRON、SANKEN等日本企业发生长期的业务关系。应当说日本企业对四通的发展是有过重要帮助的。日方对四通的控制是为了利益;而四通的反控制,除了利益方面的考虑,还有企业尊严和安全方面的考虑。日本人清楚这一点,所以也时不时地“拿”我们一把。
四通打字机诞生以来,我们的字库一直采用日立公司的芯片,由三井进口给我们。后来打字机卖火了,可能是日立的字库供应不上,也可能是三井想多赚一点钱,在未事先告知的情况下,三井用一批韩国产的芯片代替日立的芯片。四通方面不知道,装到机器上一用,发现出字不全,经过查对发现产地变成韩国的了,而且从示波器上看到韩国芯片反应速度慢,波形也不正常,压根不是我们一向使用的日立芯片。
我们提出交涉,向日方要求索赔。日方百般解释就是不承认错误,也不答应赔钱。大家僵在那儿,打字机贸易有中断的危险。这无论对日方还是对中方都可能造成严重的损失。日方派中村部长带着中入纯先生到北坞村的合资公司谈判,我方参加谈判的有段永基、我以及贸易部的一位干部,谈了一会儿段永基临时有事先走了,留下我和那位贸易部的干部继续会谈。段永基刚走出大门,日方的中村部长勃然大怒,拍着桌子指责我们不遵守合同。我是第一次看到日本人如此发火,也许是他们觉得在这件事上中方太不通融、太不给面子了,也许是段永基走了他们觉得是一种侮辱。此时我已经是主谈代表,见他们失态,我反而异常冷静,坚持不赔偿不行。最后日方只好同意,下批货物我们可以少付一部分货款。
另一次见日本人发火,是1991年中与三井、富士通谈判深通公司合资条件的时候。地点是我们在深圳租用的宿舍区的会议室里。日方有三井的中入纯及富士通的两个人,我方有我及范为强副总经理。日本人谈判一向精细,准备充分,利益问题上从来不让步。这一次为技术使用费的问题我们争论得很厉害,一直讨论到后半夜才勉强达成一致。中入纯经常与我们打交道,有经验了,还算沉得住气,但富士通的两位早已怒火中烧。当我提出协议的修改部分不能只有一份日文文本,必须同时翻译出一份中文文本时,富士通的一位先生愤怒地把手中的铅笔摔在桌子上,笔一下子就摔断了。好在中入纯先生很快把译文拿出来了,我看没有问题了,便笑着说:这位先生不必忍耐了,我们签字吧。
另一次是在深通运营半年之后,按当初与日方签的合同,我们的进货达到一定数量且国产化能力达到一定程度后,日方必须降价一定百分点。但我方条件达到后,中入纯突然从日本打来电话,不但不降价,反而因日元升值要求提高进货的价格,我当即拒绝。我们签订的合同相当于期货的性质,无论后来发生什么变化都应自己负责。但我考虑到日方的具体困难,同意暂时可以不降价,但决不同意涨价。僵持了几天后,日方发来最后通牒,意思是到当天下午五点,如果我们仍不答应他们涨价的要求,下批货物便无法提供。
事情到了千钧一发的地步,大家开始担心起来。因为弄不好可能会影响深通的出货,也会影响四通打字机的销售,损失太大了,影响也会很坏。但我同样知道,如果这次让了步,我们今后就被他们欺负定了。
下午了,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大家都看着我,我不动声色。眼看快五点了,手下人问我怎么办?我说绝不让步!他们说那影响可就大了。我说不会,我们受影响,日本人受影响更大,而且我们的要求是合理的。
五点整,中入纯准时从东京打来电话,问我:“李先生,那件事该你答复了,你到底怎么想的?”我说:“中入纯先生,我们经过认真的考虑,我觉得我们不能再做任何让步,你们必须按已经签定的合同供货。”中入纯在电话的另一端沉默几秒钟,让步了,说:“好吧,我们按李先生说的办。”
这一类事情和处理走私事件一样,都锻炼了我在重要时刻处理复杂情况所需的判断力和意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