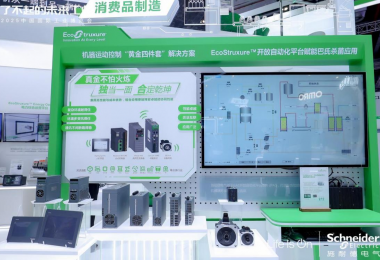6·11倒段事件
从进入四通的第一天,我就与段合作,他为人如何,以及工作中的情况如何,我非常清楚。但王安时所说段在其他方面的事情,我并不知晓。这次七董事联手“倒段”,事前我并不知情。但是段从沈手中接了总裁一职之后,独断专行引起共愤是在意料之中的。尽管他们也有各自的不满:沈的权力被段夺走,是段多年最主要的权力斗争对象;王缉志除了开发工作被边缘化不得志之外,其妹妹王缉惠在合资公司任办公室主任期间也被老段排斥,以致长期郁郁不快(我每次从深圳回京,她都在我面前哭一次),最后得骨癌而死;储忠是万的弟弟,“六·四”后,段、沈排斥他及其父,不满是肯定的。
至于王安时的翻脸,据说是段在香港背着王搞了一些自己的东西,让王觉得段在耍心眼,有意疏远自己。没有段的合作,王安时在四通的地位和利益都受影响。也有人说,段想将四通运作到香港上市,一旦成功,王安时主管的香港四通的地位将被取代,王安时对此心怀不满。李文俊、王玉钤、马明柱、朱希铎则基本是对段的工作作风强烈不满而加盟讨伐队伍的。
相当长一段时间(大约六年),段把王安时当做最信赖的高参、最亲密的合作者;王也把段当做自己在集团最可靠的代理人。两人里应外合,共同为公司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也共同搞了其他一些不为人知的东西。有时人们对他们中的某人有意见,但投鼠忌器,常常不敢说。如今哥俩儿反目,把所有事儿都抖搂出来,必欲置对方于死地,给人的感觉挺恶心的。
与会的人都会想:如果老段真的做了这些很不应该的事情,那么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王安时不大都是他的同伙吗?现在你们之间反目,却要把我们拉进来当炮灰。如果非要打倒谁,你们两个都该打倒。
而对于我,段在最近几年确实在戒备我、疏远我,我对他也有许多的不满。如果这件事是其他人牵头,我也许会考虑。但王安时和沈国钧牵头,就让人很不放心,有一种利用我们这些人的感觉。另外我想到,此时让我发言,无疑是落井下石,置我于不仁不义之地,反而让人耻笑。我不该被王安时当枪使。
我知道,如果我真的站起来迎合王安时,以我跟老段长期工作的关系,以我富有煽动力的讲话,段永基凶多吉少。此时王安时在等着我,会场里的人都在看着我,等我发言。
我却出人意料地说了这样一句话:“对不起,我保留发言的权利。”
这时的段永基面对声势浩大的反对力量,正以示弱的方式躲避着。或者一声不吭,或者发言的时候用一种示弱的口气。他的辩解此时显得那么苍白,那么可怜。一向思维敏捷、能言善辩、呼风唤雨的老段成了一条任人敲打的“落水狗”。前后落差如此之大,我看了反而对他有些同情:他毕竟一直是我的领导,我们曾亲密合作过。在合资公司、在OA本部、在四通最危难的时刻,我都得到过他的充分信任和支持。尽管我对他的一些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有看法,甚至反对,但让我翻脸无情、投井下石我做不到。
当天晚上段永基打来电话:“李玉琢,谢谢你!今天真是千钧一发,呼之欲出。”看来,他对我是否发言实际上也是十分担心的。
五年来,我一直在段永基左右,同属“合资企业派”。在别人看来,我是段永基最亲密的战友。尽管我的直率在很多时候让他下不来台,但我们总体上合作是默契的。他也以为我受了王安时的挑唆肯定会发言,其实段永基想错了。尽管我不知道王安时那么多内幕,但在这样重大关头发泄个人怨气不是四通高层应有的水平。
这一天的事情在四通内部被称作“6·11倒段事件”。
第二天晚上,“倒段派”在北京图书馆对面的奥林匹克饭店又开过一次会,有人通知我参加,我借故推辞了。据说在那次会上,王安时提出段永基下台后由他担任四通总裁的建议。从事后的情况看,王安时借“倒段”的机会上位的意图显然没有得到多数人的响应。想想看,谁会同意由曾与段沆瀣一气、身份已非中国公民、并在香港四通拥有股份的王安时来领导四通呢?他会比段好到哪里去?经过此次会议之后,“倒段事件”归于失败。
乍起时来势汹汹,一场以打倒段永基为目标的内斗风波,随着挑头的王安时落寞地飞回香港,老沈等人被老段分化、瓦解(有没有其他交易不得而知),逐渐偃旗息鼓。
这次事件在四通的历史上,算是比较严重的一次内部斗争,反映出四通内部的矛盾已经达到了有你无我的地步,也反映出老谋深算、聪明过人的老段在四通呼风唤雨多年,此时竟然那么不得人心。而“倒段派”表现出的政治斗争方面的幼稚以及水平,也让人不敢恭维。
此事件的化解,还有另一个重要因素起了作用。那就是胡昭广领导的开发区管委会的态度,他们明确表示对段永基一如既往的支持。他们没有看好其他人,更不希望四通陷入混乱对开发区可能带来负面影响。
段永基躲过一劫,四通内的裂痕已经形成。有的人因此离开了四通。
“二王”的不同遭遇
1992年7月,“倒段事件”在开发区主任胡昭广的周旋之下,段永基拉住和摆平了沈国钧、李文俊、马明柱、朱希铎、郑洪如等几个关键人物,终于风平浪静。段永基度过了四通历史上最惊险的一次危机。而此次事件造成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四位副总裁王安时、王缉志、张齐春、孙强的辞职。他们在公司巨大的政治危机中没有离开四通,却在内部斗争中伤心而去。
新闻报道说,这四个人一起办了个“新四通”公司,其实没有。是王缉志这位四通打字机的总设计师拉来一家新加坡的公司合资兴办了新四通,但这个公司后来并没有成就什么气候。
张齐春是和光大集团合作共同成立了注册资金2000万元的“光大系统集成公司”。
孙强后来做什么不得而知。
王安时离开四通的时候,拿走了一大笔钱(将香港四通19%的股份变现)。香港四通的积累中,有相当部分是四通集团和合资公司在香港四通的留利。如果知道有这一天,当初应当慎重考虑通过香港四通转手进口的必要性。这也是四通当初设立公司时不规范、不严格、不审慎带来的后果。
王缉志是一个很单纯的知识分子,为人相当谦和。他离开四通后在网络上连载《开发打字机的故事》,其中曾说他一辈子最大的遗憾和错误,就是当年万润南让他当北京合资公司(索泰克)的总经理时,他拒绝了,结果总经理的职位就归了段永基。
在我看来,从管理能力和水平上说,他肯定不如段永基。尤其在政府公关、协调各方面关系以及经营管理方面。但正因为他不会、也不愿做这样的一些事情,倒可能更依赖和信任其他干部去做,也不会有那么多的权力斗争。从这个角度说,公司也许不会有那么多无谓的磨难。
不过,王缉志在四通的遭遇还真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联想也发生过柳、倪分手)。他后来被排除在MS-2406的研发之外,是不应该的,毕竟四通里面他在技术方面是最拔尖的,他的人品也是可以信赖的。他在《开发打字机的故事》中写道:“我虽然是四通集团主管开发工作的执行副总裁,但是我能够支配的开发费用还不到公司总营业额的0.3%……尽管按照国家和开发区的规定,公司可以提取营业额的7%作为开发费而纳入成本,但这些开发费提了之后都不知道干什么去了。公司请人吃顿饭,唱一次卡拉OK,动辄可以一掷千金,甚至万金,为总裁办张高尔夫会员卡可花几十万上百万,可是我要调用几万元的开发费都要经过很麻烦的手续。每当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的时候,就要我们写科技开发项目的可行性报告,但这是写给银行和政府看的,因此而得来的科技贷款却用到了其他方面,用去炒股票、炒期货、搞房地产。”
如果四通能在产品研发方面多下些功夫,少在权力斗争上花那么大的精力,四通可能会是另外一番模样。
王缉志和王安时都是四通的创始人,都是公司董事,而且后者还是前者加盟四通的引路人,但是几年过去,两人同时离开四通收获却完全不同。王安时退出四通时盆满钵满,王缉志辞职时却两手空空。王缉志在这方面的讲述也是书生气十足:“在打字机销售最红火的时候,一个2401经销员的脚上,一双皮鞋就值三五百元,而我当时每月工资收入只有560元,列在全公司第19名……1993年,四通与我签了一个协议,承认我是四通创始人之一,并答应给我创业股,其数值与其他董事相同。四通股票在香港上市之后,我要求四通兑现该承诺,四通公司答复说,我们答应给你的是创业股,但是现在公司并没有创业股,所以不能给你股份……这种事发生在一个高技术公司里难道不奇怪吗?”其实,后期的四通主旋律已经不在产品开发上,甚至也不在企业经营上,高层很多人的精力大都消耗在权力斗争或个人利益得失一类的事情上了,在对待人的问题上早已失去初创时的热情和厚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