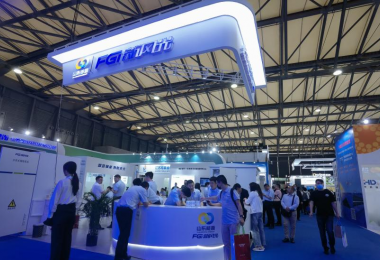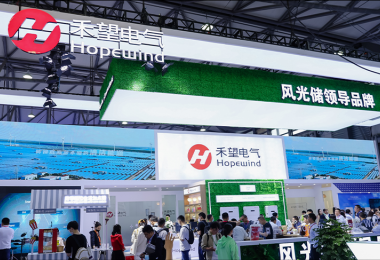我们提出交涉,向日方要求索赔。日方百般解释就是不承认错误,也不答应赔钱。大家僵在那儿,打字机贸易有中断的危险。这无论对日方还是对中方都可能造成严重的损失。日方派中村部长带着中入纯先生到北坞村的合资公司谈判,我方参加谈判的有段永基、我以及贸易部的一位干部,谈了一会儿段永基临时有事先走了,留下我和那位贸易部的干部继续会谈。段永基刚走出大门,日方的中村部长勃然大怒,拍着桌子指责我们不遵守合同。我是第一次看到日本人如此发火,也许是他们觉得在这件事上中方太不通融、太不给面子了,也许是段永基走了他们觉得是一种侮辱。此时我已经是主谈代表,见他们失态,我反而异常冷静,坚持不赔偿不行。最后日方只好同意,下批货物我们可以少付一部分货款。
另一次见日本人发火,是1991年中与三井、富士通谈判深通公司合资条件的时候。地点是我们在深圳租用的宿舍区的会议室里。日方有三井的中入纯及富士通的两个人,我方有我及范为强副总经理。日本人谈判一向精细,准备充分,利益问题上从来不让步。这一次为技术使用费的问题我们争论得很厉害,一直讨论到后半夜才勉强达成一致。中入纯经常与我们打交道,有经验了,还算沉得住气,但富士通的两位早已怒火中烧。当我提出协议的修改部分不能只有一份日文文本,必须同时翻译出一份中文文本时,富士通的一位先生愤怒地把手中的铅笔摔在桌子上,笔一下子就摔断了。好在中入纯先生很快把译文拿出来了,我看没有问题了,便笑着说:这位先生不必忍耐了,我们签字吧。
另一次是在深通运营半年之后,按当初与日方签的合同,我们的进货达到一定数量且国产化能力达到一定程度后,日方必须降价一定百分点。但我方条件达到后,中入纯突然从日本打来电话,不但不降价,反而因日元升值要求提高进货的价格,我当即拒绝。我们签订的合同相当于期货的性质,无论后来发生什么变化都应自己负责。但我考虑到日方的具体困难,同意暂时可以不降价,但决不同意涨价。僵持了几天后,日方发来最后通牒,意思是到当天下午五点,如果我们仍不答应他们涨价的要求,下批货物便无法提供。
事情到了千钧一发的地步,大家开始担心起来。因为弄不好可能会影响深通的出货,也会影响四通打字机的销售,损失太大了,影响也会很坏。但我同样知道,如果这次让了步,我们今后就被他们欺负定了。
下午了,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大家都看着我,我不动声色。眼看快五点了,手下人问我怎么办?我说绝不让步!他们说那影响可就大了。我说不会,我们受影响,日本人受影响更大,而且我们的要求是合理的。
五点整,中入纯准时从东京打来电话,问我:“李先生,那件事该你答复了,你到底怎么想的?”我说:“中入纯先生,我们经过认真的考虑,我觉得我们不能再做任何让步,你们必须按已经签定的合同供货。”中入纯在电话的另一端沉默几秒钟,让步了,说:“好吧,我们按李先生说的办。”
这一类事情和处理走私事件一样,都锻炼了我在重要时刻处理复杂情况所需的判断力和意志力。
唯一的绿洲
南国三年,我偏踞深圳自成一统,虽然孤单,但却是我24年企业生涯中最有收获的历程之一。用四通集团副总裁郑洪如的话说,深通公司是当时“四通唯一的绿洲”。无论是企业文化、精神面貌,还是经营效益、管理水平,都是第一流的。四通集团旗下的企业盈利的后来越来越少,深通却一直是盈利的。
1994年底,深通账面上还有1400万元现金没有动。段永基知道了,对此大为惊讶:李玉琢你们账上怎么趴了这么多的钱?他提出要调走一部分钱给集团用,我未同意。除了已经对他的不规范做法有了些警惕外,还因为深通公司毕竟也是合资企业,我要对它负责任。如果将来对不上账,我将难以交代。这也许是1995年初要把我调开的重要原因。
这种外放的经历,不管派遣者用意如何,对于被派遣者来说,都是一种难得的锻炼。后来到华为,把并无市场竞争力的莫贝克调理到位,四年后以7.5亿美元的价格卖给艾默生,得益于此;离开华为,接手濒临倒闭的利德华福,并把利德华福办成行业内旗帜性的企业,也得益于此。
而同一时期的四通,却加速了它的衰败进程。
四通是我24年企业生涯中,受到熏陶和锻炼最大的企业,也是我遇到过的企业政治最复杂、权利斗争最激烈的企业。这也许是改革开放未久,“文革”的残留还影响着人们;也许是四通在创办的初期缺乏成熟的经验,留下了一些后遗症;当然也存在加入四通的人鱼龙混杂,利用公司制度和管理的不健全,钻空子;但无论怎样,只要领导核心目标一致,团结一心,不断成熟,企业照样可以在风浪中前进。但四通的问题在于,首先出问题的恰恰都在上层的核心领导或主要领导,这样一来,四通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倒沈”活动
“六四”之后,沈国钧由于一直在南方,没有过分介入运动,被推到前台,顶替万润南留下的空缺,担当四通集团的董事长和总裁。风头一旦过去,沈国钧的位置成为权力斗争的焦点。
沈国钧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系,长时间在科学院计划局工作。1980年前后,为院部管理项目被派到计算中心工作。四通成立不久,他抛弃科学院的铁饭碗,与万润南一起创办了四通。沈国钧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坐而论道,能说不能做。
在运作企业方面要说掌管大局,可这么多年他连珠海的一家小公司也没办出名堂。将刚刚卷入政治风暴、人心惶惶、业务几近停滞的四通交给他,让其担任四通新掌舵人挽狂澜于既倒,的确也难为了他。
后来有一篇文章在描述这段历史的时候这样写道:
在万离开后,由沈国钧任总裁的四通增速开始直线下滑,年均增长只有16%(营收1988年10亿,1990年是13亿),这跟前三年300%的年增速比简直是天上地下。
文章继续写道:
因为在这两年里,四通已积累起来的相当规模的资产不但没有发挥应有的规模效应,反而因利益一直无法落实到个人而导致内部人开始胡乱处置自己属下的财产。这才有了一家IT公司居然在全国各地买地的情形,甚至还在杭州买了800亩墓地,而仅地产一项四通就沉淀进资金达数亿。段永基说:“当时四通内部很混乱,根本没有时间管理业务。”
文章还写道:
而主导中文打字机业务的段因为比较用心和相对专注因而业绩表现出色,加上得到了政府的认可,到1991年时段得以正式以常务副总裁之职执掌四通。
这篇文章写得虽然大体属实,但文章的指向和最后一段的内容,很容易让人怀疑是否是段永基的授意。
万润南走后,论能力和威信,段永基肯定在其他人之上。居于沈国钧之下本是一件情势所迫的事情。但风头一过,在沈国钧这样一个不明白的人领导下工作,不仅段永基别扭,很多干部也都不习惯。
大概在1990年中,段永基曾召集一些副总裁包括我、陈永长、朱希铎、郑洪如等十来个人在林业大学的一个会议室开会,议论的主题就是沈国钧当总裁是否合适的问题。
另一次在夜间,司机把我们拉到什么地方大家也未搞清楚,电话通知也没说开什么会。到那之后一看基本还是那几个人,话题仍然是沈国钧,段永基把沈国钧当政之后的一些不太规范的个人行为说与大家。
两次会的与会人员都不是傻子,并没有人真正表态并与之呼应。虽然大家对沈国钧的能力与水平不敢苟同,但也没有谁希望外部创伤刚刚愈合的四通,再次面临内部分裂的局面。两次会我也一言未发,我是觉得这种做法不够光明正大,有点阴谋诡计的味道。让老沈下台我并不反对,但为什么不可以在董事会上公开讨论呢?暗地里搞动作终非君子之风。
此后,老段和老沈之间的矛盾逐渐公开化了。人与人之间的别扭必然影响到业务开展,也在干部中产生了很不好的消极影响。老谋深算的沈国钧自然不会听任宰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