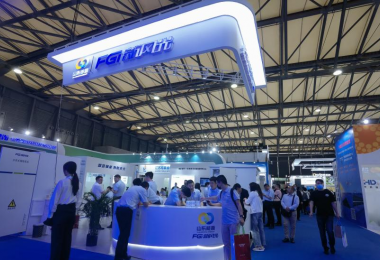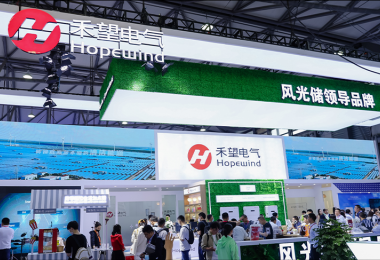农场四年多的岁月,在我的一生中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起承转合,承前启后。而下乡后的最初一段,又是那么的纠结、唏嘘而关键。
老人家的一声令下,我们这些响应文化大革命号召的青年男女(当时称为红卫兵),在城里折腾了两年多,又奔向农场“经风雨见世面,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学校第一拨下乡的,在68年的7-8月,是到丁玲等大“右派”劳动改造的、坐落在兴凯湖边的友谊农场。我们很多人对此不明就里,初期基本持观望的态度,但后来的形势一阵紧似一阵,去与不去几乎成了革命与不革命的分水岭,便纷纷报了名。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哈尔滨北边300多公里的海伦农场,在此之前是黑龙江劳改厅下属的第十八劳改支队。那一年海伦农场前后三批接受鸡西知青近四千余人。
11月3日上午,鸡西火车站的站台从未有过的拥挤,几千家长为一千多自家的孩子送行。到了火车上才发现,母亲给我装在书包里的鸡蛋、水果挤丢了许多。当时笼罩在人群上空的,是类似于战士上前线的那种悲壮。当火车启动的汽笛呜响的时候,火车上下几乎一片恸哭,车厢里有的学生甚至跳脚大哭。不知为什么,我不仅没哭还觉得奇怪:我们仅仅是到农场劳动,而非去送死,何悲之有?我和同班几位同学的格外冷静,让站台上等的亲人心安许多——我们的几位家长几乎都没有哭,他们和我们成了当时情景下的另类。几十年过去了,鸡西车站送行的那一幕我至今难以忘记。
火车到达海北站时,天已经黑了,外面下着凉丝丝的小雨。我们一千多人肩扛手提着自己的行李在吆喝声中,又爬上来接我们的卡车,几经颠簸,到达三井子——海伦农场的总部。当人们把我们领进一个长长的房子里时,我们看到的是屋子两边惊人的百米大炕。我们一直朝里走,里面居然还有一间小房子,我们几个高中的同学把行李往炕上一丢,就算占领了这个地方。后来有人告诉我们,我们住的房子原来是劳改犯住的,在我们到来之前的一个月劳改犯才匆匆撤走。我们这些来自小城市鸡西的孩子,虽然对农场并不陌生,但我们毕竟是第一次远离父母,第一次到一个遥远而荒僻的地方劳动、生活,没有人知道这里等待我们的是什么,也不知道我们在这里呆多久,更不知道前途在哪里。
幸运的是,我们班的几个人被分配到米面加工厂的榨油车间。所谓幸运是与其他人比较而言,比分到农业连队成天在田地里摸爬滚打的要好,毕竟风吹不着雨打不着;比在米面车间那些扛麻袋走跳板的人要好,毕竟没有那么累且危险。但油坊工作的热、脏以及三班倒却不是他人能够体会到。估计目前在中国这种人工的、笨拙的榨油方式早已绝迹了。油坊车间地面又黑又滑,一般在里面工作时,哪怕是冬天,都要拖掉衣裤,只能穿一条大裤衩干活,不只因为脏,而且热得要命。轧油的大致程序如下:黄豆洗净之后要放到大铁锅里用热气熏蒸,大约个把小时,把几乎半熟的黄豆用一种简单的机器把它压扁,然后把这种叫做“豆坯子”半成品装到大约一寸高的铁圈里,一层层摞起来,每一层之间用薄铁皮隔开,大约十层左右,要码齐,然后推到榨油机下,人工转动丝杆,一圈一圈的转动,越压越紧,就会有黄色、透亮的豆油从每一层的缝隙间流出,汇成细流,淌到一口埋在地下的大油缸里。
在油坊工作的好处逐渐现露出来:每每干到夜深人静,我们需要小憩时,便有人在火炉上放一口铝锅,舀一大勺子自己刚刚轧出的豆油,烧开了,把我们带的馒头、窝窝头切开了丢在里面,炸得焦黄,大吃一顿,剩下的装到饭盒里带给要好的同学们。同时告诉他们,不要当着别人的面吃,知道的人多了,不仅难以应付,而且也容易出事——毕竟是不允许的。刚到农场时,由于劳改犯撤退的仓促,很多菜都冻了,冻了的萝卜、白菜经过大锅一煮,有一种难闻的猪食味儿,不要说多难吃了。在那样的条件下,我们能吃到炸馒头,无异于天堂的生活。还有一点不好,是满身的豆腥味儿,缺乏洗澡的条件,下班时在水龙头下接一盆水擦擦就不错了,有时连擦都不擦就回到宿舍睡觉,因此连被窝里都充满豆腥味儿。那时候也有人装得很正经,别人休息时抽烟、闲聊、炸馒头,他却在幽暗的灯光下,掏出一本老人家著作的单行本儿,在那里看——我们很怀疑这种学习的真实性、目的性,这种故作积极进步的姿态,让同学们极为反感。那时我是榨油车间一个班的班长,负责码垛的,那是我下乡后的第一份工作,在那里我工作了大约四个月。
农场环境毕竟陌生、艰苦,记得有的人到农场第二天就打包回鸡西了。当时我们很瞧不起这类回去的人,把他们看做逃兵。不久,有人报告说女宿舍里有人又哭又笑,精神不正常,我们这些男生爬到窗户上往里瞧,果然,几个女生坐在炕上身体一摇一摆,连哭带笑个不停,不知怎么了。有人说这叫“癔症”,是精神压力太大时的一种反应,奇怪的是,这种病似乎有传染性,很多宿舍女生都犯同样的毛病,一直闹腾好几天,后来不知怎么就又都好了——像03年的SARS一样,来去无踪。在我们的男生宿舍里,由于人太多(大约百人),每天睡觉前,一片混乱,有的人在炕上连比划带唱,有一句至今记得:我那老祖母还在遥远的穆陵河那边……,固然有玩儿闹的成分,但想家是当时一种普遍的情绪。转眼到了第二年春节,青年们纷纷回家去了,我没有回家,我觉得面对这一切需要一种决心和勇气,我写信告诉老爹妈:儿在农场一切均好,春节需要有人值班不能回家,切勿惦念。
69年3月,我被调到农场中学当老师去了,那一段油坊榨油工的生活结束了。2005年,我曾回过海伦农场一趟,到已盖成楼房的农场中学看过,还到当年的米面加工厂的简陋的大门前站立良久,眼前的一切都变了……离开农场时,我让车在路边停下来,装了满满一包黑土回北京,至今保存着。